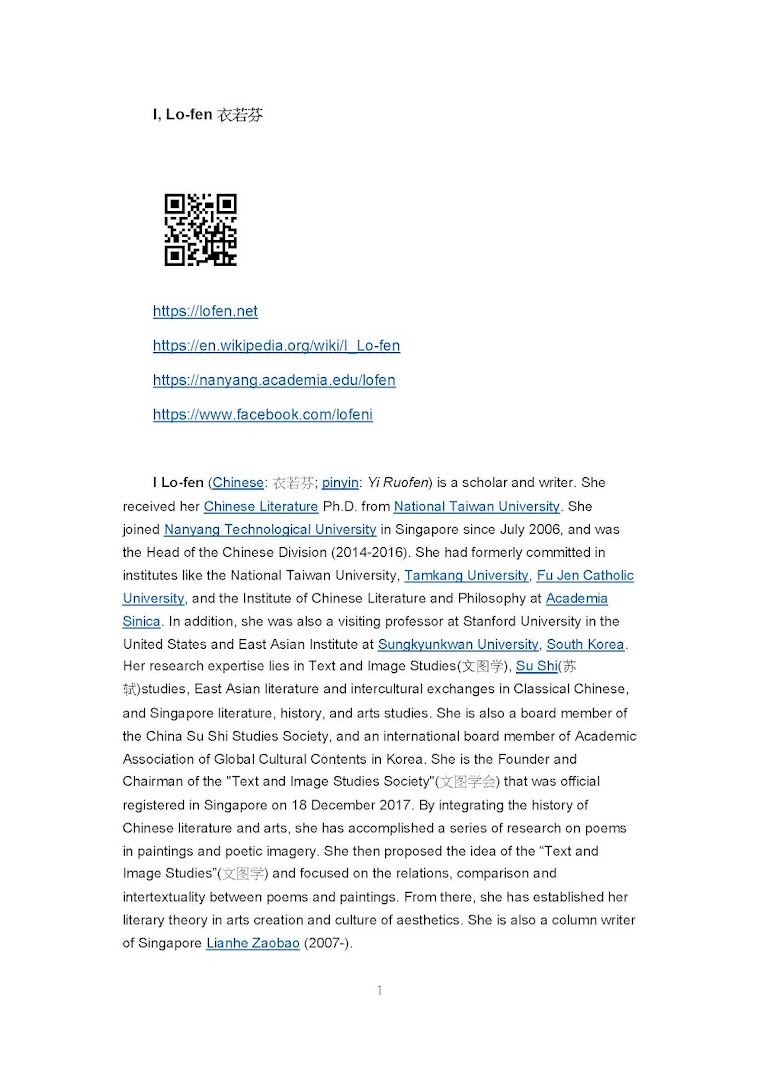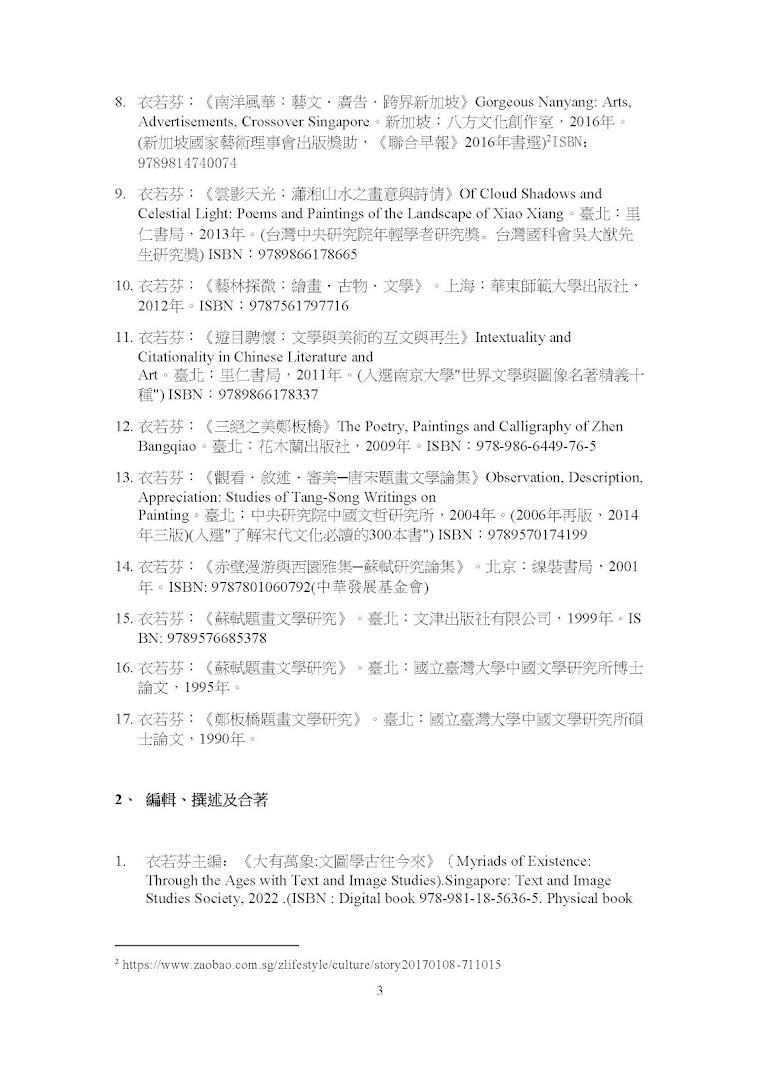桄榔庵遺址
 有此衣說
有此衣說
「姐姐,你拍這菊花,這菊花很美。」
我回頭看見她,大約十歲的小女孩,頭髮紮起馬尾,皮膚黑亮,一雙炯炯有神的大眼更顯清澈。
我朝她點頭,微笑一下,繼續拍著豎立在菜園爛泥裡的這座殘碑。碑身有四分之一陷入雜草土塊,有明顯龜裂後修補的痕跡。除了碑頭「重修桄榔庵記」幾個篆字還依稀可見,碑文漫漶不清。碑陰有「中正」兩大字,不曉得是當時立碑時已有,還是後來刻上。
「姐姐,你踩到她家的葱了。」身後多了兩個年齡相仿的小女孩,馬尾女孩提醒我,這裡可是私人菜園子。
我收起相機,問她:「你家在哪裡?」
四下有農舍和豬圈,剛才走進這不及兩米寬的桄榔路,除了「但尋牛矢(屎)覓歸路」,還和大腹便便的老母豬、活蹦亂跳的花公雞、小母雞「擦身而過」。
「我家住在桄榔庵。」她說。
我聞聲一震,「桄榔庵」的主人,可是九百多年前的東坡先生哪!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我指指「重修桄榔庵記」的殘碑。
「蘇東坡。」她和她的朋友異口同聲回答。
「那邊還有東坡井。」她伸長手臂往右前方比畫。又說:「那邊叫坡井村。」
「東坡居士謫於儋耳,無地可居,偃息於桄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東坡的〈桄榔庵銘〉記敘了他卜居海南儋州的情形:「海氛瘴霧,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入娛。」東坡本來借住於官舍,後被逐出,只好在城南買地築屋,屋附近是桄榔樹林,所以取名「桄榔庵」。
「桄榔樹呢?」我問她:「就是那三棵嗎?」
三個女孩大笑:「那是椰子樹啦!」
果然是都市來的無知姐姐啊!(雖然被叫姐姐有點不好意思)
「桄榔樹長得怎樣?」我環顧周圍。
「沒那椰子樹高…」「葉子大大…」「本來有的,全部死光砍掉了…」她們爭先恐後地說。
沒有桄榔樹的「桄榔庵」。東坡說此地「生謂之宅,死謂之墟」,有老死南荒的決心。兩年多後,他獲赦北歸,終焉常州。「桄榔庵」畢竟是東坡一生少有的「不動產」,歷代前往儋州的文人和官僚,不免到此緬懷憑弔,或是在原址修建蘇公祠,紀念一代文豪。
從元朝到清朝,以桄榔庵為基地的蘇公祠範圍逐漸擴大,曾經有正殿五間、講堂五間之規模。現存「重修桄榔庵記」的殘碑,就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所立。可能碑文字跡太過模糊,有說此碑立於明末;有說立於清朝道光年間,碑文詳細內容也不清楚。到了民國初年,昔日屋宇被夷為平地。
現在遊客到儋州,大多會參觀以東坡海南友人黎子雲的「載酒堂」為基地,修建得詩意古雅的「東坡書院」。原興建於北宋的儋州孔廟在文化革命中被焚毀,東坡書院於是取代孔廟,成為百姓祈求考試金榜題名的聖殿。
走在儋州中和鎮,被家家戶戶門口紅通通的楹聯吸引。左右長幅對仗工整,門楣橫披齊全。沿著門框上端,浮貼五張紅紙,象徵五福臨門。
無論是新穎樓房,還是陳舊宅厝,那樣誠心一筆一畫的書法,不是工廠大量印刷的產品。使人好奇:這個街上趕著牛車、屋後劈柴燒火、牆角排列醃菜甕缸的古鎮,怎麼把〈赤壁賦〉化為窗戶上方的一道紅光──「清風明月」,「清風明月」是春聯?不求財富?不必權貴?
「結茅得茲地,翳翳村巷永。」東坡在遷居桄榔庵之夕,聽見鄰居小兒誦讀,欣然作詩,說「兒聲自圓美」。即使如今只剩一方殘碑,來自海角天涯的訪客,仍然能在此地感受到千古風流的文化底蘊。
「蘇東坡的家沒有了,姐姐,要不要去看東坡井?還有水呢!」馬尾女孩還沒等我答應,就呼朋引伴跨過桄榔庵菜園子口的垃圾,往前領路去了。
(2011年1月23日,新加坡「聯合早報」,時為東坡冥誕975年後一日)
My home is Guanglang temple
Published on : 23-Jan-2011
Assoc Prof I Lo-fen, Division of Chinese, NTU wrote an article in Lianhe Zaobao cherishing the memory of Su Shi. Su Shi was a writer, poet, artist, calligrapher, pharmacologist, and statesman of the Song Dynasty in ancient China.
Read more in:
Lianhe Zaobao, Page 19
2011年2月21日《聯合早報》讀者回應
“为什么你们一直要来看一块石头”?
(2011-02-21)
早报导读
● 林冠雄
南洋理工大学衣若芬副教授的文章《我家住在桄榔庵》(见1月23日联合早报《想法》版),令人激赏。她在文中的一句话:“即使如今(桄榔庵)只剩一方残碑,来自海角天涯的访客,仍然能感受到千古风流的文化底蕴”,也是掷地有声。
三年前,我也到中国海南岛再作了一次文化之旅。那天和朋友在海口租了德士,往西南下到儋县,参观了“东坡书院”,之后即往访“桄榔庵”。德士师傅不知道“桄榔庵”在哪里,好不容易在一间店屋前问到一位妇女,她往店后一指,说:“在后面。”到后面一看,原来只有一块残碑一片乱草,令我大失所望。回到店屋前再向这位妇女道谢和道别时,她说:“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和其他一大堆游客,一直要来看这块石头?”
这位儋县的村妇显然是不知道“桄榔庵”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北宋大文豪苏东坡(1036-1101),在贬琼时期〔1097-1100〕的住家。北宋末年,中国政治腐败,苏东坡屡遭迫害。在儋县,苏东坡被朝廷派人赶出官舍,露宿在桄榔树下。幸好他在这遭受危难的时刻,儋州太守张中(因与苏东坡亲近,后来也被朝廷逼害至死)和海南人民,见义勇为,帮他在桄榔树下建了这间“桄榔庵”,苏东坡才有了栖身之所。
一代天才苏东坡,集思想家、书法家、诗人、词人、画家等于一身。他在各方面,尤其是诗词创作方面,可说是成就斐然。现在全世界研究苏东坡(苏学)的人,何止千万。
苏东坡的思想,照耀千古。他的著作已经是世界的文化遗产。我希望:
一、中国有关当局能重建“桄榔庵”。苏东坡的黎族学生黎子云的住家(载酒堂;苏东坡教书的场所)现在已变成了美丽堂皇的“东坡书院”,没有理由苏东坡自己的住家却只存下一块残碑和一片乱草。这样是多么让国际学术界人士以及游客觉得惋惜、失望。桄榔庵也凝聚了人民对苏东坡的爱戴以及体现了汉黎民族的和谐。因此,桄榔庵是值得重建的。
二、新加坡是华族文化的福地。华族各种文化艺术如书法,民歌等,在此蓬勃发展。华人传统节日如华人新年、中元节等都得到热烈的庆祝。我国的裕华园里也竖立了八尊中国伟人如孔子、屈原等人的塑像,以宣扬中华传统文化思想。我希望新加坡有关当局或是民间组织也能找一适当地点,竖立一尊苏东坡的塑像,以宣扬苏东坡思想,那就是主张:忠于国家、民族团结、巩固国防、乐善好施、直言敢谏、打击贪官污吏、发展教育,和睦友邦、善待政敌、孝敬父母、珍惜友情等等。苏东坡是儒家的完人,是知行合一的文化巨人。苏东坡思想是全人类的遗产,新加坡也可以宣扬和提倡,他的思想很适合新加坡的国情。
谢谢衣副教授的上述文章,抛玉引砖,让我有机会在此重谈此题材。如果我的建议能被接受,定能再稍微增强我国的文化底蕴。中国就是因为文化底蕴深厚,才能有今天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切从头越。
 新加坡海南會館 黃遵憲楹聯,李俊賢攝
新加坡海南會館 黃遵憲楹聯,李俊賢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