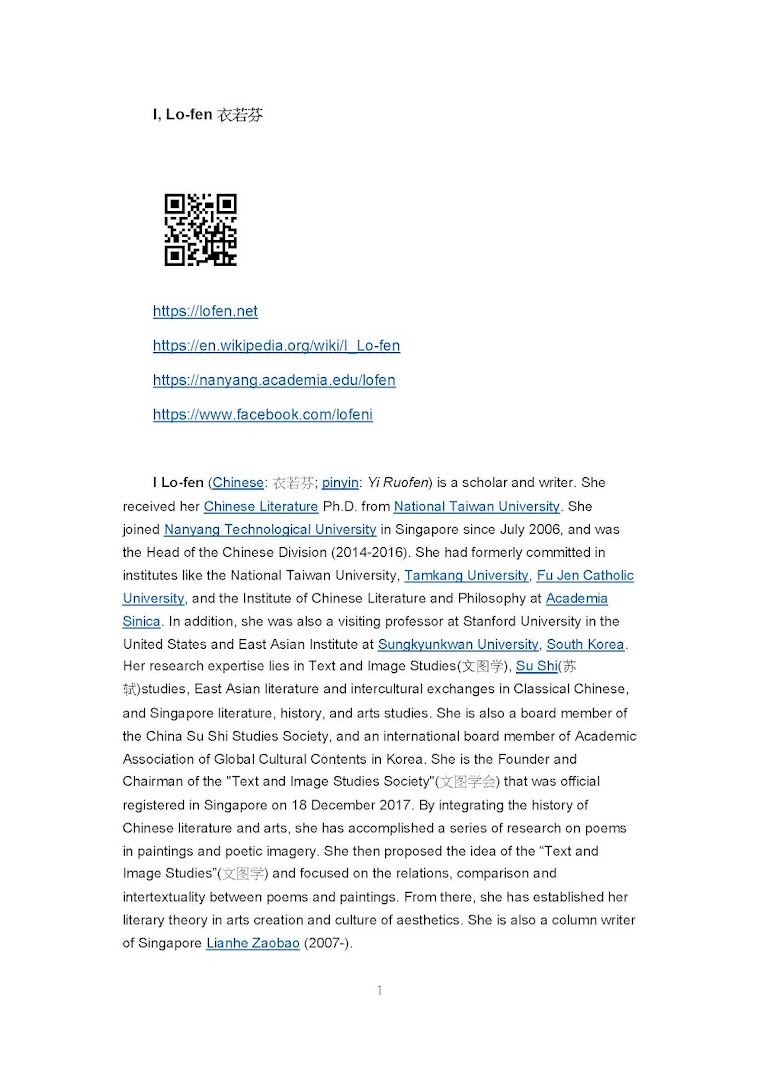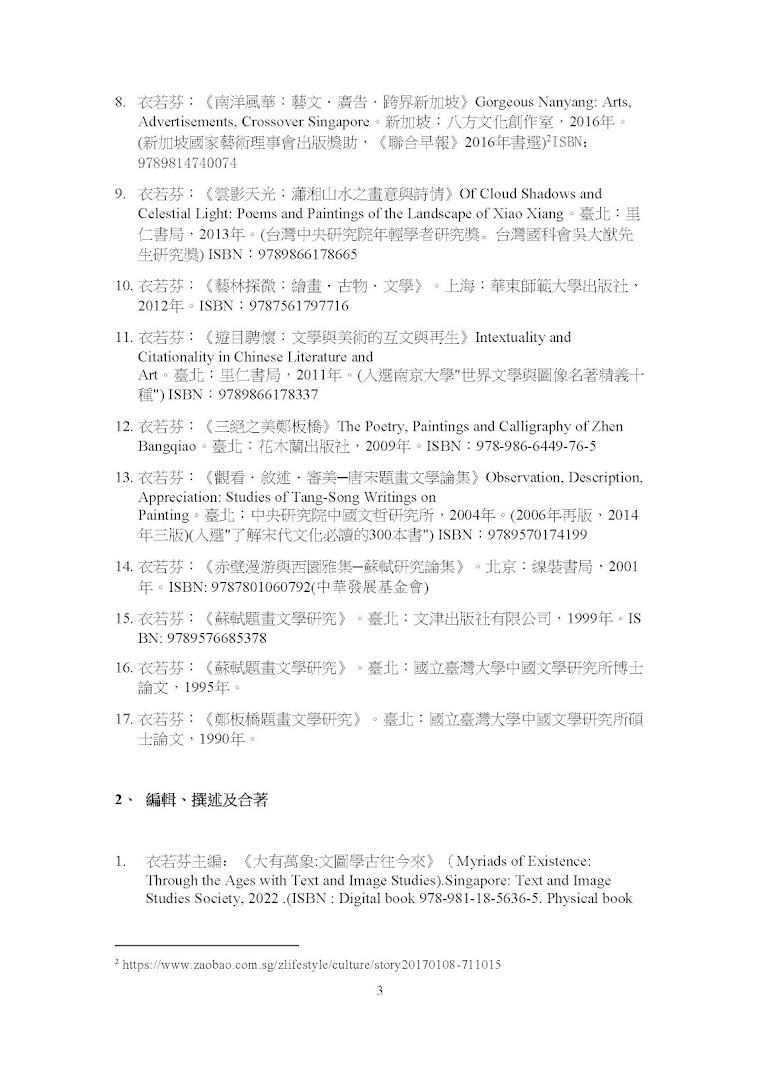跟AI(人工智能)學寫詩?是的,你沒看錯。
新年伊始,你的願望和計畫是什麼呢?2022年,我期許自己繼續學習,終身學習,尤其是補充對於科技和文明關係的知識。上過“企業中高階經理人AI培訓班”的網路課程,取得證書之後,讓我更認識人工智能的趨勢和影響。
2020年,我應台灣東華大學邀請演講,談了AI生成詩,舉了我用“文圖學”的英文名稱“Text and Image Studies”製成文字雲(word cloud)讓人工智能“少女小冰”看圖作詩的例子,讓線上和現場的觀眾投選,認為少女小冰生成的三首“詩”,是否就是“詩”呢?投選的結果,半數贊成;28%反對;22%表示不知道。
這和圖靈測試(Turing test)不同。圖靈測試算是盲測,也就是判斷者只就AI生成的結果決定是“人類智能”還是“人工智能”。我的詢問,是已經知道評判的對象是人工智能生成物,再來決定是否合乎“詩”的條件,關鍵在於“什麼是詩?”一位中文系的女同學說:從文法和句式看來,少女小冰生成的文字符合詩的要素,也能讓我們感受到其中含有的人類情感,所以是“詩”。一位資訊工程系的男同學上傳了三張照片到少女小冰的網站,發現文字的內容重複單調,認為設計有局限,稱不上“詩”。
我持續思索人工智能生成詩的問題,寫成論文,在2021年的“南京論壇”發表。觀眾大多是中文系的學者,對這樣的話題感到新穎有趣,我被點評老師形容像金庸小說裡的黃蓉和(滅絕)師太,以虛指虛,高竿高明。我想,大家對於AI生成物,包括音樂和繪畫等等的態度,除了探討藝術的定義(算不算是“詩”?)、科技威脅(人類藝術家還有活路嗎?),以及創作倫理(剽竊AI生成物充當自己的作品)之外,還可以有人機合作的豐富可能性,比如2019年少女小冰和200位作者合作出版詩集《花是綠水的沉默》、2020年AI和科幻作家共同寫作《共生紀》。
對於一般人,AI生成文字的步驟,教我們明白文學創作的過程,神奇的靈感即使不存在,也可以用圖像或想像來寫作。五世紀的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早已經歸納作詩的原理:“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應物”、“感物”是藝術創造的起心動念,AI沒有人的心念,憑藉的是大數據和圖像辨識,從參與少女小冰的研發團隊的台灣大學林守德教授剖析得知,AI原來是這樣生成詩:
1.圖像輸入→卷積神經網路(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處理
2.圖像辨識→預處理圖片關鍵字→物象+形容→前後遞迴 (recursive
generation),正向與反向生成模型→造句
3.N-gram 語言模型,詞頻
4.連續句:將上一句的資訊轉化成編碼,傳給下一句
從研究人類大腦的運作應用開發人工智能,其實也可以反向操作於我們的寫作。姑且不細講專有名詞,如果你有興趣練習寫詩,步驟是:
1.
首先拿一張你“有話想說”的圖像,或是想像某個場景畫面。
2.
想適合這圖像的字詞,最簡單的是形容詞加圖像裡的物象。然後找反義詞,組合成前後對照的句子。
3.
上傳你的句子到網路上,檢查是否通順合乎語法,或是模仿既有的相近句子,加以修改。
4.
用同一圖像或另一畫面重複前面三階段,形成第二句。將兩個句子並列閱讀,想想有沒有意義和音韻(如果寫歌詞)的邏輯關係。
寫舊體詩絕句的話,四句就行了。這種刻板的方式可能會令一些創作者反感不屑,我也不是這樣寫作的,不過,經常被詢問如何寫作,一言難盡,不如給個模板套路。這個模板套路未必磨練得出精妙的詩句,至少讓作詩沒那麼玄乎。有機會讓我教寫作課的話,或許可以和學生們玩一玩。
要不要把“寫詩”當成你的新年新氣象?我總結跟AI學寫詩,順手拿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