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衣若芬设置,AI生成 |
在新加坡友人社交平台上看到滨海湾花园的巨型古典美女,由色彩斑斓的鲜花组合而成立体半身立像。从中国传统小说到现代景观装置艺术,游客纷纷仰首合影。
这位佳丽是谁呢?
我一时想到:崔莺莺?红娘?
佳丽身后高于头顶的白底大弧形是什么?圆光?
不可能是妈祖吧?
看了新闻报道,才晓得是为了迎接蛇年,打造的《白蛇传》主题装饰,那“圆光”,其实是绘画西湖山水景致的油纸伞啊。
怎么我一眼看不出她就是白娘子呢?白娘子不是应该全身素净,穿着白色的衣衫吗?这位白娘子好缤纷华丽呀。
我又想,如果是全身素净,穿着白色衣衫的白娘子,大过年的,会不会让人觉得太过单调平凡,甚至有些丧气呢?还是缤纷华丽一些好。
新加坡华人大概对白娘子的故事不陌生。电视剧如《白蛇后传之人间有爱》、《青蛇与白蛇》;方言戏比如粤剧、琼剧、潮剧、福建歌仔戏都演过白娘子的故事。再加上近年大陆的动画电影,吸引大批年轻观众,我就指导过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谈从明代冯梦龙拟话本小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到动画电影《白蛇:缘起》和《白蛇2:青蛇劫起》的改编与创新,学生反复推敲自己喜爱的作品,将阅读和观影的体验结合文图学的理论,写来得心应手,乐在其中。
那么,非华语和方言的族群,除了依靠英语字幕,还有没有接受和欣赏白娘子故事的情形?
1934年,印尼华人郑丁春(The Teng
Chun,1902-1977)拍摄马来语恐怖电影《水淹金山》(Ouw
Peh Tjoa),并出口到新加坡。其后续集为《白蛇之子》。
1973年,林怀民在台湾成立“云门舞集”。云门舞集的海外第一场演出就在新加坡,演的是《白蛇传》(The
Tale of the White Serpent),无需语言。
罗靓教授在《世界的白蛇》(The Global
White Snake)书中,提到出生成长于新加坡的林晓英(Cerise
Lim Jacobs)
创作英文歌剧《白蛇夫人》(Madame
White Snake)。林晓英在媒体访谈中讲述儿时看粤剧、林黛的黄梅调电影《白蛇传》给予她的印象和冲击,她认为《白蛇传》最动人的是“异类”希望拥有和人类一样的感受,勇于追求爱情和抗争命运。
林晓英希望通过《白蛇夫人》打破令人厌倦的西方歌剧中“疯女人”的刻板形象,这是2005年她送给丈夫Charles的75岁生日礼物。《白蛇夫人》在2010年2月在波士顿举行世界首演,同年10月在北京演出前两天,Charles不幸病逝。2011年该剧的作曲家周龙获得普利策最佳音乐奖。
《白蛇夫人》由男性演唱青蛇的女高音,这似乎是20世纪末以来《白蛇传》逐渐植入性别题材的延续。2017年新加坡野米(Wild
Rice)剧场的音乐剧《白蛇娘娘》(Mama
White Snake)“玩”得更大,和原著也走得更远。王爱仁(Ivan
Heng) 和魏铭耀(Glen
Goei) 分别反串白蛇与青蛇,法海由女演员西蒂(Siti
Khalijah Zainal)反串。
《白蛇娘娘》由 黃淑貞(Pam Oei )执导,剧本由 亞非言(Alfian
Sa’at)
编写,一反传统的男女情爱主题,将主角设定为白蛇的儿子孟(Meng)。孟受不了母亲和姑姑青蛇的极度保护,离家出走,到法海开办的武术学校习武。他爱上了法海的女儿(是的,法海有妻子有女儿),并且从法海得知母亲和姑姑为蛇妖的秘密,展开对自我身份的探寻。
融合英语、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和部分华语,以及中国戏曲、武术、西方音乐,《白蛇娘娘》充满幽默、冒险和温情,娱乐效果满满。如同梁海彬的剧评《错位,才能产生思考》,我们的思考在于大胆的创新,即使偏离原著,如此多元而杂糅的“天马行空”,更富有新加坡本地特色和趣味。
乙巳木蛇年,木为青色,不知道青蛇今年会不会跃登主位?要说那翠盖红颜的滨海湾花园巨型古典美女,像不像青蛇?
2025年2月1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善若水”专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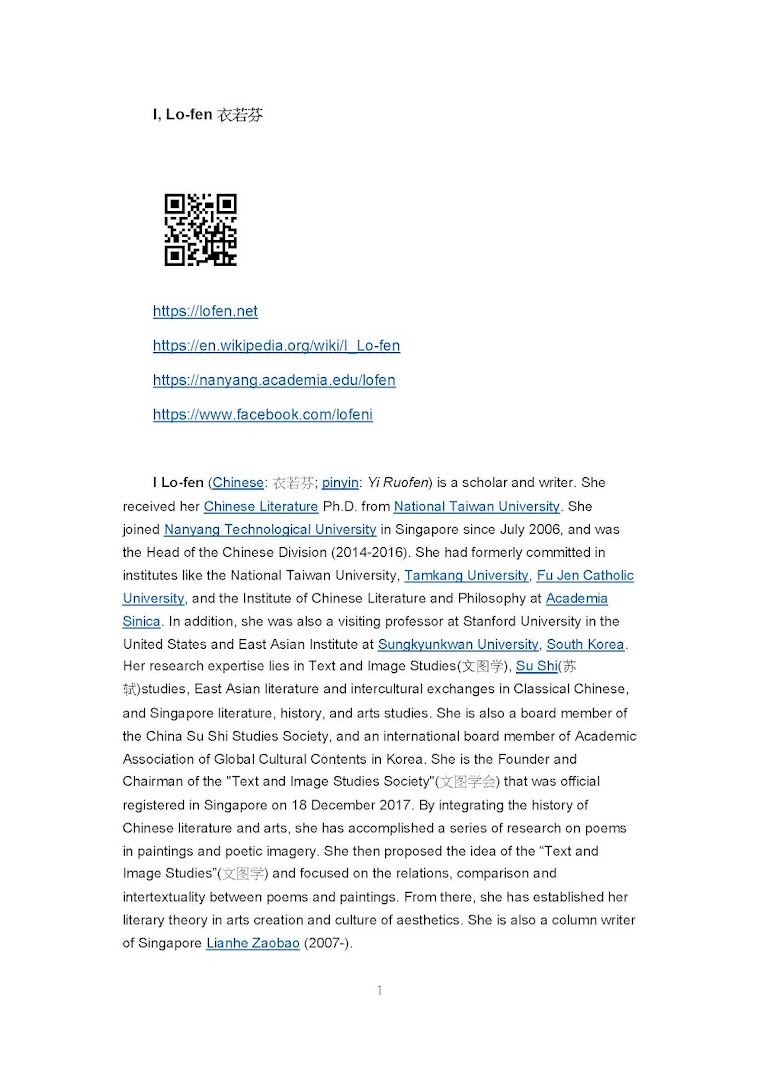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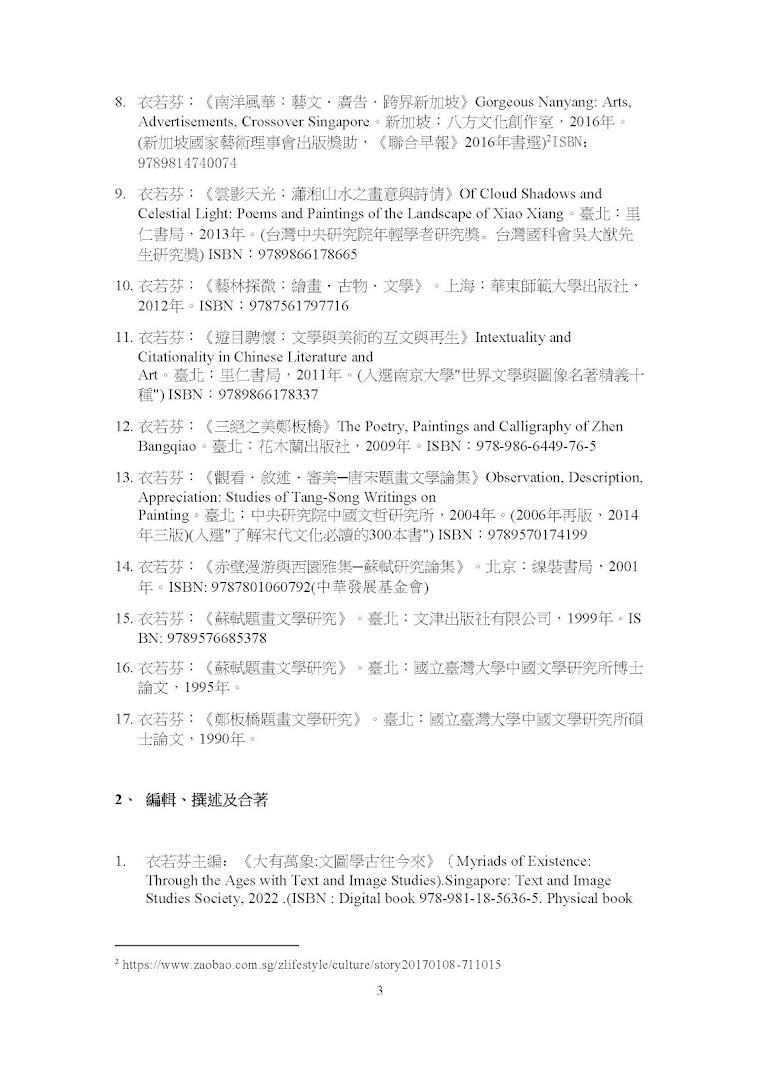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