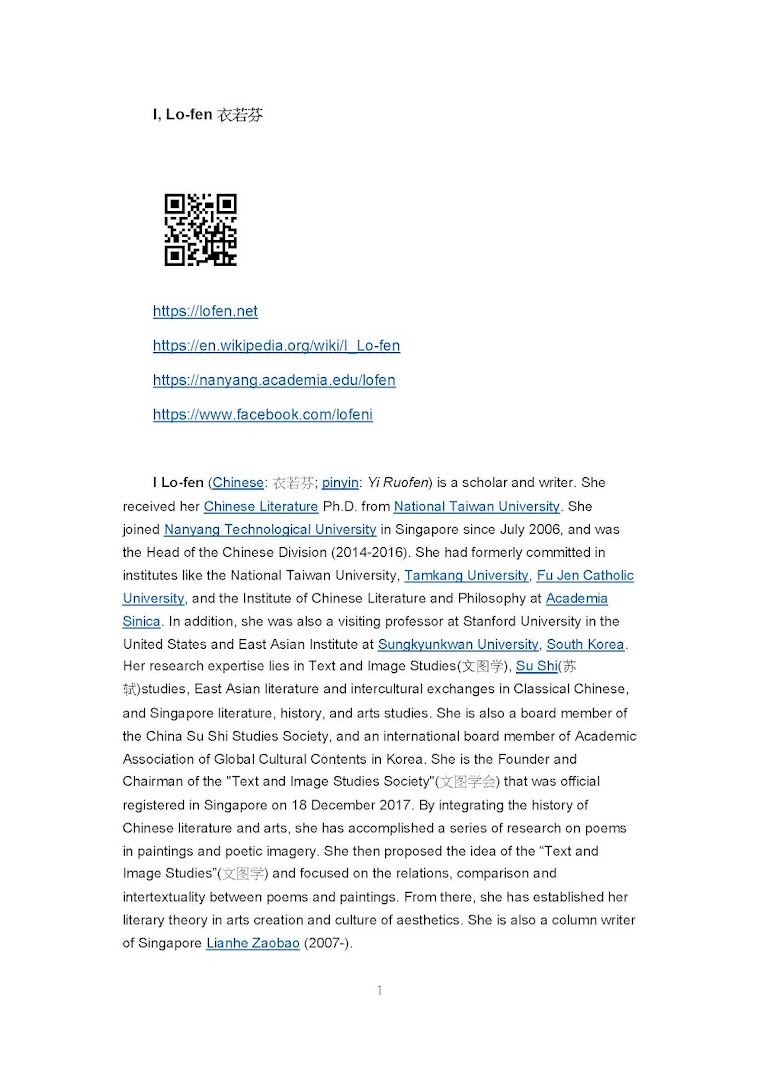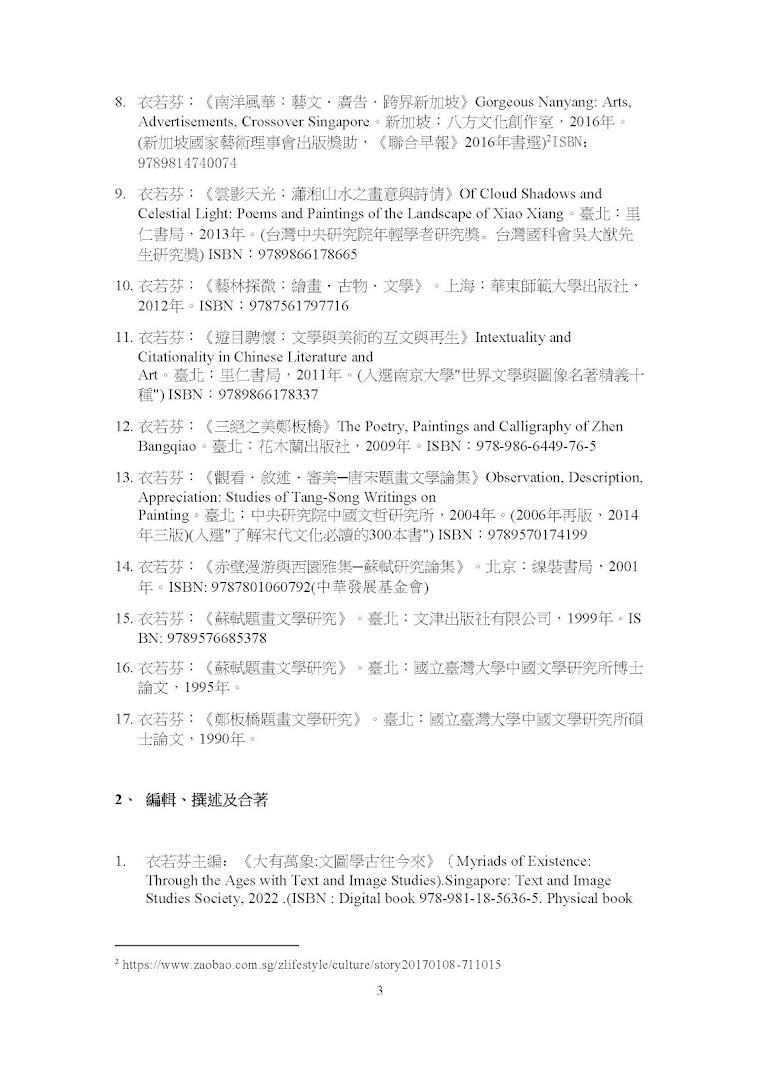喝完那一小口微凉的茶沫,我心满意足地赶往下一个展厅。
终于,在研究和发表宋徽宗《文会图》二十年之后,以“沉浸式体验”(Immersive
Experience),在杭州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亲身进入了《文会图》的空间。
以往隔着玻璃展柜观看展示品的方式,近年来增添了新的趣味,我们不只是“看”展品,而是身临其境地进入展览所营造的情境与氛围中,通过多种感官调动(视觉、听觉、触觉、嗅觉,互动行为),产生情感共鸣和深度参与,称为“沉浸式体验”。
最早的沉浸式体验来自视觉。这类展览往往利用大规模投影、环绕式屏幕和动态光影,让观众被图像包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北宋郭熙《早春图》,描绘万物生机蓬勃时节的大自然;通过科技设计和体感侦测,观众可以走进山雾缭绕、溪水潺潺的画境,伸开双臂,仿佛鸟儿展翅翱翔,飞到峰顶,旋转视角,发现不一样的风景。那一刻,《早春图》从“被观看”变为“被参与”,观众也超越画框,从“旁观者”变为“共创者”。
除了虚拟的绘画影像,更直观的方式,便是复制/还原画面为真实的场景,比如眼前的《文会图》。《文会图》描绘幽静的园林中垂柳依依,繁树掩映,几位士人围坐在铺满花果美馔的长案旁,愉悦谈笑,气氛雅逸从容。侍女与仆役穿梭其间,还有一位执拍板的男子似乎要开始余兴节目。此时酒宴将尽,画面前方正准备着点茶。
展场布置了三折屏风,中央悬挂《文会图》。屏风前偌大的长案,再现画中物品。观众如果坐在环绕长案的藤椅,便宛如扮演了画中人物。于是我随性坐下,拿起酒盏,朝旁边正在插花的汉服仕女致意。
声音,是沉浸式体验的第二层通道。音乐、环境音、甚至沉默,都能建构出空间的情绪。《文会图》的
一隅石桌上有香炉、书册和古琴,暗示即将的乐音;实景的《文会图》安排了仕女弹奏古筝,营造古典的历史氛围,吸引观众接近驻足。
如果说视觉与听觉构成了感官沉浸的前奏,那么触觉与嗅觉则让沉浸进入身体的深处。
在兰州敦煌艺术博物馆复制敦煌佛教洞窟外面,放了一块砂砾岩,看似不经意的装饰,其实是让观众可以触摸,感觉石头的质感。砂砾岩容易风化,试想如此肌理上图绘的壁画如何不易保存?
香港艺术馆《好物有型》展,观众点触屏幕回答气质测验问题,可以得知适合自己格调的专属香味,并且嗅闻香味的样品。4种个性类型呈现的4种艺术家风格,不但令观众理解,也随之趋于认同。
至于五官五感中的味觉在文物艺术展览时较为操作复杂。展览不是饮食售卖,只是摆放食物的话,观众的体会稍嫌单调。与其推出成品,不如表现过程,实景《文会图》设置了现场示范点茶,将以往像宋徽宗《大观茶论》记叙的内容,配合《文会图》的画面,具体展演。
这位点茶女士将白茶粉放进茶碗,注入70度以上的热水,然后拿茶筅反复环回击拂,《大观茶论》详细说明了7次注汤的步骤细节,逐渐搅打出乳白色的泡沫—--这就是苏东坡词里的“雪沫乳花浮午盏“啊!
现代人喜欢的咖啡拉花,一千年前的宋代人早就玩过了,而且不必依靠牛奶,仅仅将热水点在搅打好的茶泡沫,形成色差水纹;或是拿茶勺轻划,花鸟虫鱼、诗词文字,栩栩浮现,所谓的“注汤幻茶”、“分茶”、“茶百戏”、“水丹青”,真是巧思灵动。
悠扬的古筝乐曲声萦回着雅集的余韵,我抚触那仿汝窑的茶盏,想起当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报告《文会图》,“师祖”方闻教授的赞赏和嘉勉:“没想到中文系出身的学者能够研究得这么透彻。”我后来告诉方教授,我是他得意弟子石守谦老师的学生,算是他的“再传弟子”了。他笑得合不拢嘴,频频点头。我研究《文会图》的文章名为“天祿千秋”—-感恩天赐的福禄,给予我们艺术审美沉浸至生命底层的喜悦。
2025年11月2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