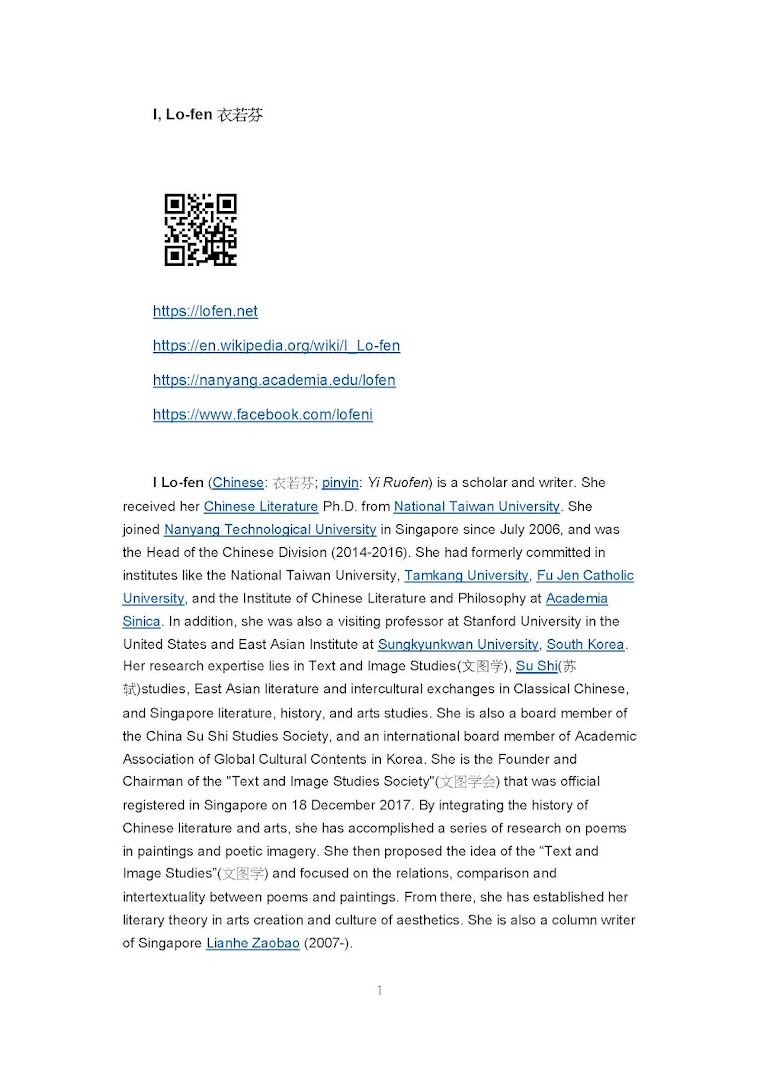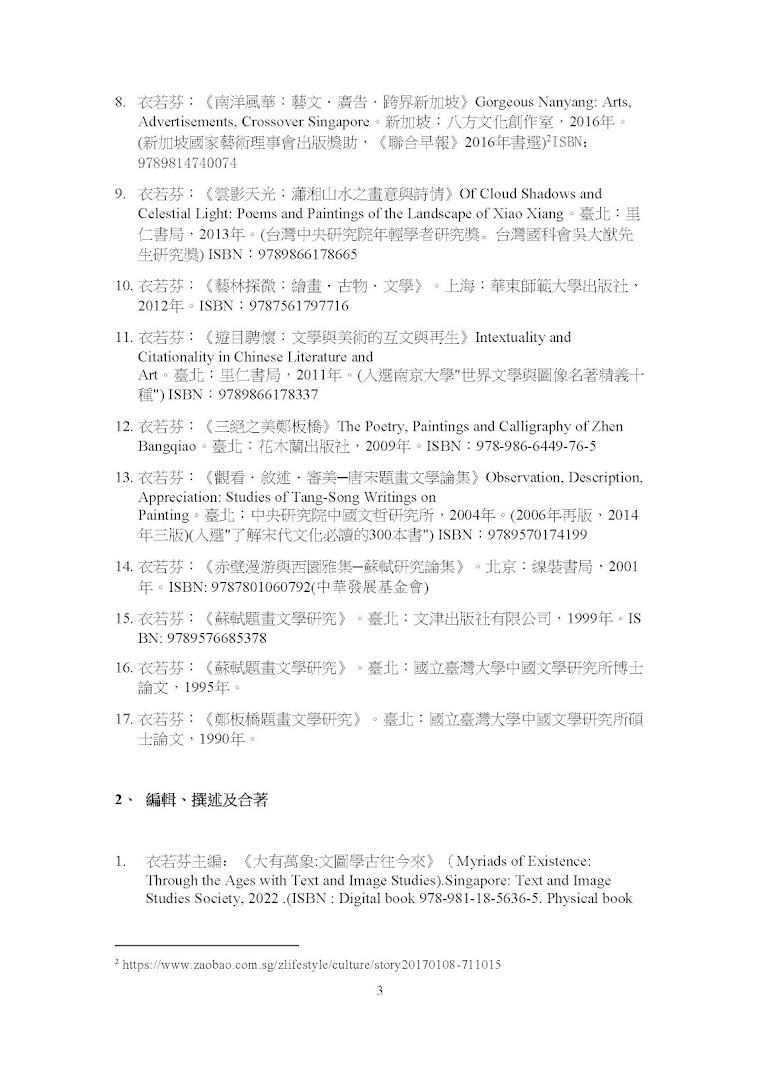網路的迅速和強大散播力量,讓製作影片的團隊小小"網紅"了一下。連我這位"發起人",也受媒體邀約採訪。
記者問我,為什麼拍這段影片?
學生們用影片記錄活動和表達想法,是現在經常使用的方式。過去在南大中文系的社群媒介裡,也都屢次展現。不同的是,這次攝製組的同學大部分是今年四年級的應屆畢業生,頗富情懷。其中有兩位具備拍攝電影的專業技能和經驗,從編劇到演出,全部由學生們操辦。
「讀中文系沒前途?」「新加坡華文不重要?」影片從五個角色引發了一些話題,自我解嘲,以及自我顛覆,試圖和觀眾一起思考,得到了熱烈的回應,我看著看著,也笑出了淚花。
影片完成時,恰好是大學開放日(Open
House)的前幾天,於是我們在片尾加上了歡迎大家來校園參觀諮詢的文字。
我在大學開放日在中文系的櫃台前「站崗」過好多年,注意到逐年的變化。最鮮明的是:無論是學生,還是家長,提出的問題從「中文系都學什麼」,轉向「中文系畢業後做什麼」。
關於「中文系都學什麼」,最擔心的是要學古文,要背誦很多很難的字詞詩文,要記得中國所有朝代的歷史……。也就是說,大家關心的是南大中文系的「產品」,以及使用、操作「產品」的方式、過程和「親善度」。
「中文系畢業後做什麼」的疑慮,則是朝「產品功能」的方向發展。通過四年的訓練,一個中文系出身的青年,能在哪個職業領域派上用場?
照理說,在設計產品時,就應該構想產品功能,但是南大中文系的課程包含古今中(國)外(東南亞),兼俱語文史哲,產品和功能之間並非直線的關係,用孔子的話來形容,叫「君子不器」──我們培養的,不是像器具一樣,有限定用途的學生。我對解說產品駕輕就熟;對描述產品功能嘛,稍有障礙。
因為缺乏很多不同類型的職場親身經驗。我做過的工作,都不出文化、教育、傳媒、藝術、出版,這些都是想當然爾的中文系畢業生出路。如果對方問我出路的問題,而我回答的是這樣想當然爾的答案,不但像是廢話,我自己也不會滿意甘心的。對方問我,就是想要得到超出預期的回覆,否則不必特意光臨的。
我認為,還有許許多多我們目前不曉得的工作和職業隨著世界的變化而將陸續出現。僅僅互聯網電子商務,就需求大量善於文字發想的人才,中文系正是提供人才的來源。
於是,我改口問對方:「你想做什麼?」從對方對未來的想像,反思我們的產品和功能,以及可能擴充的服務。
哈佛大學教授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在1980年代提出了多元智能(Multiple
Intelligences)理論,他曾經指出未來人才最重要的四種關鍵能力:解決重要問題、問出好問題、創造有趣的作品,以及可以和同儕相互合作的能力。這四種能力可以概括為「思考判斷」和「創意執行」。什麼是「重要」、「好」的問題?甚至,什麼是「問題」?便要靠思考判斷。人文學科研究理解的,主要就是「人」,就業市場中服務的也是「人」;而在競爭狀態下勝出的,即是憑藉創意執行,使用語言文字連結客戶端,全球除了英語,最大量的是中文。
換個角度想,換個角度看。平時很少走到辦公室大樓前的草坪,想到新書《南洋風華》裡有一張蘇雪林站在南洋大學建校紀念碑的照片,便走下去看。以後此處將會改觀,我隨手拍下了照片。照片裡,枝葉掩映,南洋大學建校紀念碑被石塊護衛著,草坡上「自強不息」「力求上進」的南洋大學校訓,只有望向華裔館才看得見。
我知道,天下的道路都是人為的,要緊的是「你想做什麼」。
(2016年3月1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