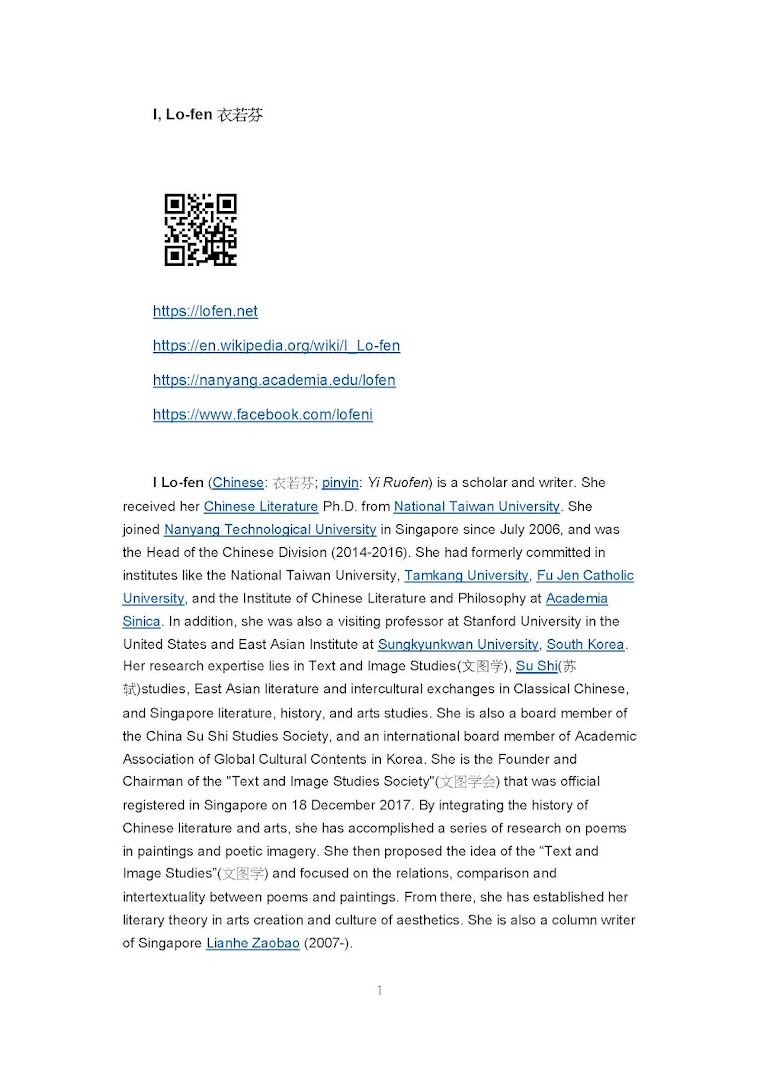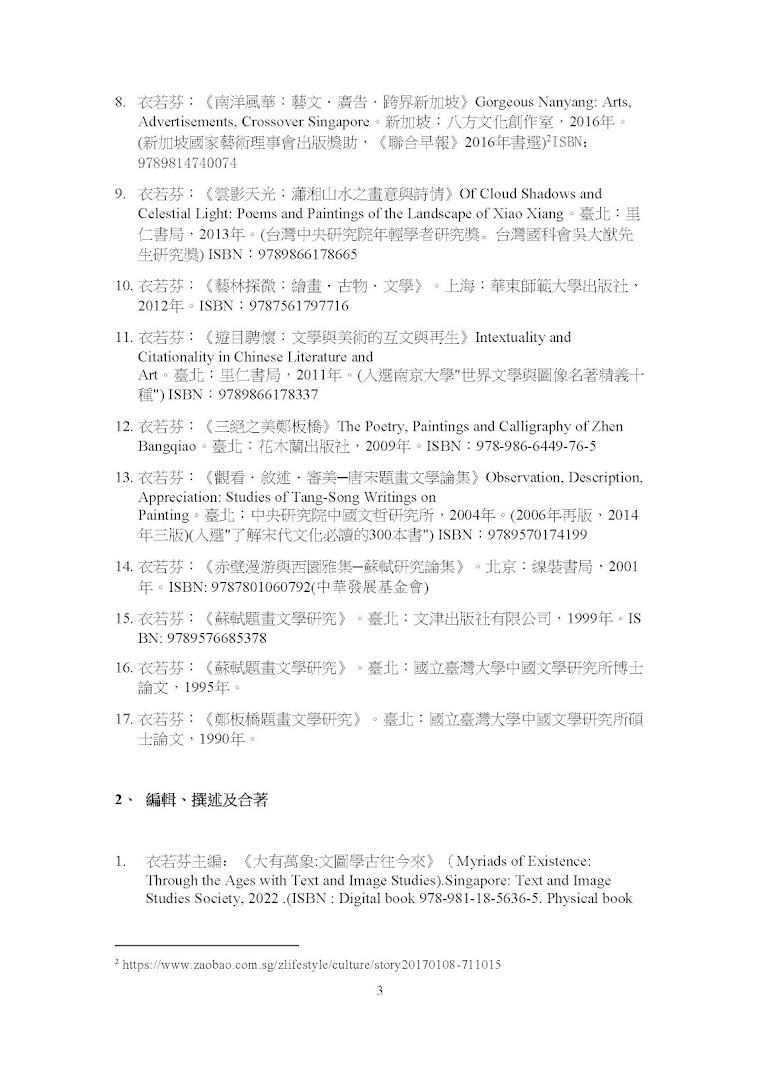|
| 照片說明:德川義親(左)。田中館秀三(中)。Corner博士(右)。那位女士身份不詳。 |
如果申請成功,新加坡植物園將是國內第一個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認可的世界遺產。
問問身邊的友人,島國有個世界遺產,什麼心情?什麼想法?
興奮、光榮、期待,增加本國自信、給金禧國慶很好的禮物…。
也有人表示「沒有什麼」。不會像一些世界遺產變成景區,參觀費用瘋漲,給政府帶來滾滾財源,新加坡植物園基本是免費向公眾開放,是不是世界遺產,影響的首不在營收利益。
以前住在大學宿舍,假日想帶孩子去植物園走走,孩子說:「校園裡這麼多大樹,還有印尼八哥和啄木鳥,這裡已經是植物園了!」
我告訴他:植物園不但有很多樹,還有很多花,是花草樹木的家,一個美麗的大公園。
帶著過去遊台北植物園的印象逛新加坡植物園,發現這裡不但清幽,還有一份雅緻。知道是英國殖民時期就成立的機構,卻總想著這裡彷彿貴族的苑囿,開放給老百姓享受些園藝的樂趣。
東方園林喜歡以小觀大,納山川天地於湖石流水,景隨物移,步步見新。新加坡植物園不刻意造景,讓人目不暇給的各種花木是主角,不待人的賞玩品評,它們在那裡自然展示自己,引發人對它們一探究竟。
是的,我們很快放棄品頭論足的主導權,花木不再是向我們爭美的少女壯男,它們是活生生萬物的一部分,類型各殊。同樣的,我們也只是萬物的一部分,膚色、語言、體態各殊。
東方園林的人文眼光難免有價值的判斷和意義的追求;而在植物園,我們只看到生命的各種表現形式。雖然人可以經由育種及雜配的手段,培養和改變植物,但那之前,思考的是認識它們、了解它們的原理,而後才是技術的操演作用。也就是說,在植物面前,沒有先驗的宇宙論和世界觀,沒有「實然」和「必然」,只有「已然」─它已經在那裡,你不必「見青山多嫵媚」,青山見你,不是青睞,也不是白眼,你是個脊椎動物。
在生物的世界,人在自己製造的戰爭中自相殘殺,能夠擺脫「敵」、「我」的對立,共同探析和理解生物世界,現在想來,也還不是輕易的事。1942年2月,新加坡被日軍占領,和所有機構一樣,植物園也被接管,當時的副園長Edred
John Henry Corner (1906-1996)在他的回憶錄裡,記敘了日據時期的生活和經歷。
Corner博士出生於倫敦,父親是外科醫生。由於天生有些口吃,他知道自己當不成老師,於是轉向生物研究,對真菌和苔蘚特別感興趣,大學畢業後便來到新加坡植物園工作。日本占據新加坡,他不忍心13年的研究心血被無情地破壞,和日本東北大學來的地質學家田中館秀三(1884-1951)一起,向有「馬來之虎」之稱的山下奉文(1885-1946)將軍直接談判,包括植物園、博物館、圖書館的文化資產都應該受到保護。
山下奉文不敢對文物造次,由於背後有軍政顧問德川義親(1886-1976)的督導。德川義親侯爵是尾張(今名古屋)德川家的第19代當主,也是個植物學家。Corner博士的回憶錄,便是在得知德川義親死訊之後寫的,出版於1981年,書名是The Marquis: A Tale of Syonan-to(侯爵:昭南島的故事)。石井美樹子於次年將本書翻譯成《思い出の昭南博物館》(昭南博物館的回憶)。
田中館秀三在1943年7月歸國,接著到任的是京都大學植物生態學家郡場寛(1882-1957)。郡場寬和Corner博士共同研究熱帶植物,催熟了Corner的「榴槤理論」。
Corner博士不諱言日本人對華人的殘酷殺害,也沒有美化和他合作研究的日本學者多麼仁慈寬大,掠奪與占有,本就是侵略者的目的。在日本戰敗後,Corner博士寫到郡場寬教授桌上的手槍,兩人的俘虜/監視者身份互換,該如何面對這樣的景況?
在Corner博士的書裡,我注意到他用了「尊敬」這個字詞,是對學問、對學者,也是對大自然的尊敬。唯有懂得「尊敬」的人,才能超越一時的對立,善待眾生。Corner博士的公子John K. Corner寫了My Father in His Suitcase: In Search of E.J.H. Corner, the
Relentless Botanist,另一視角的植物學家人生。
如果要說新加坡植物園呈現的世界遺產,我想,是我們對於人與物的「尊敬」,以及「超越」對立的態度,這無須聯合國認可。
2015年5月16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2015年7月5日,新加坡媒體報導,新加坡植物園通過申請,成為世界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