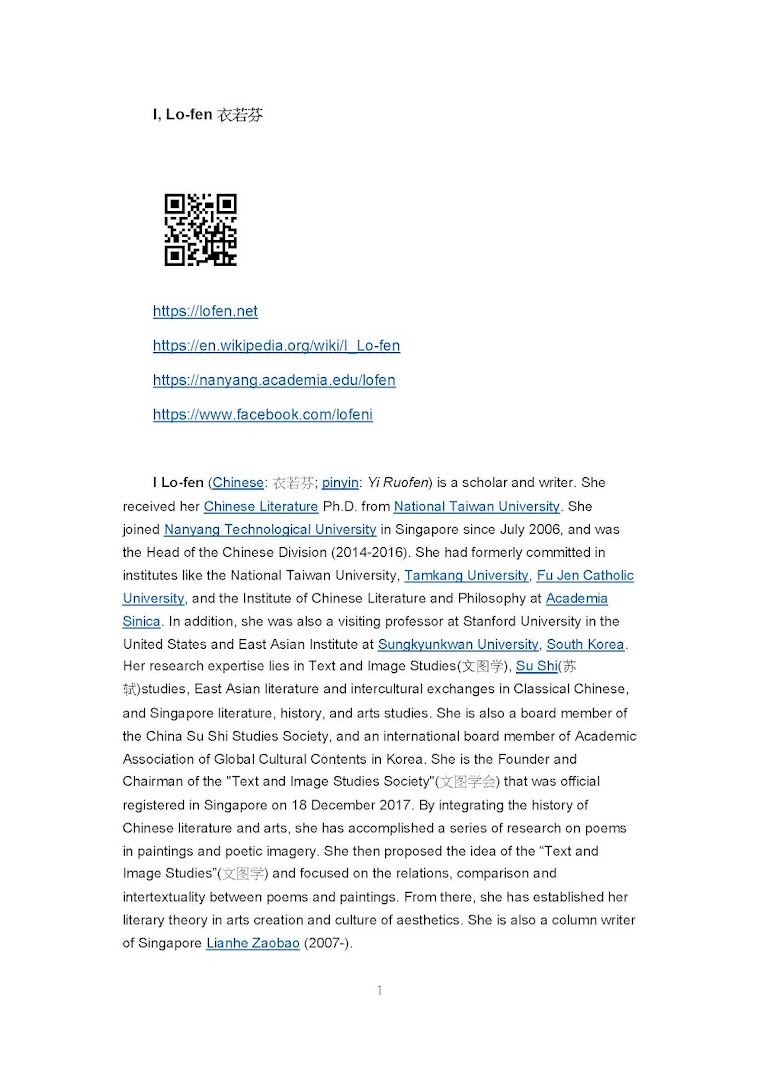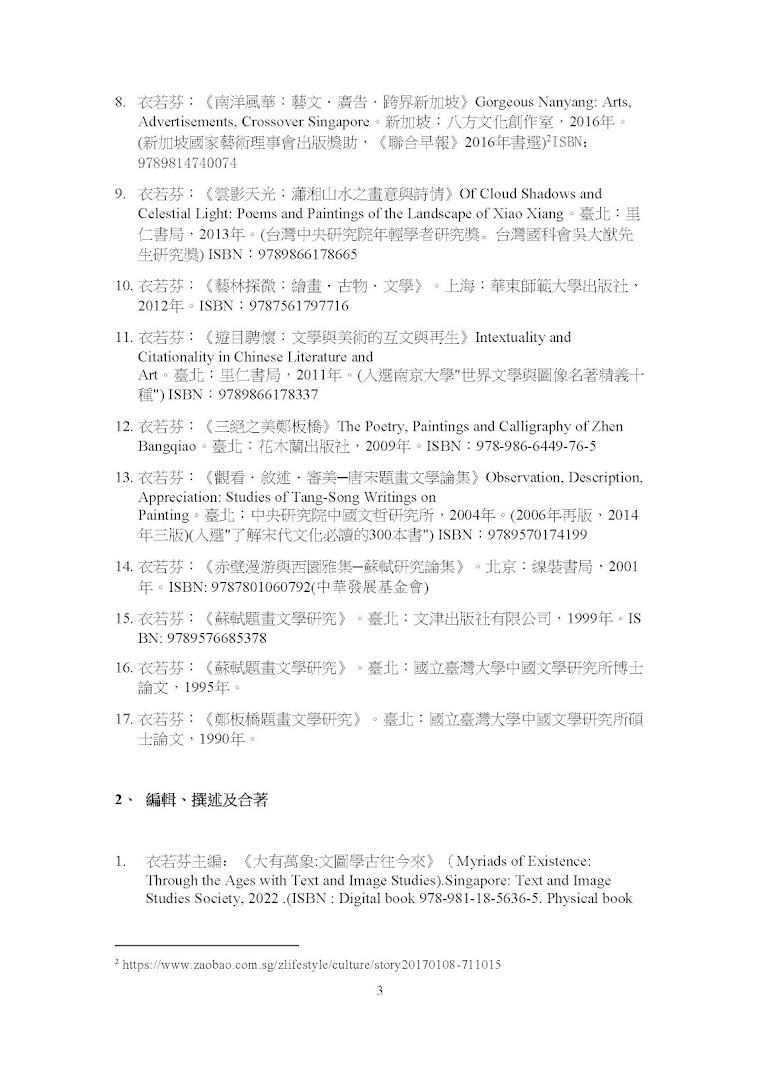2025年4月19日下午2-4点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5楼
欢迎扫码报名!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 寄自新加坡的未來回憶與幻想 https://lofen.net
 |
| 肖玉双提供 |
闲嗑嚼着怪味胡豆,呷一口竹叶青茶。小双滑动手机屏幕的影像,说:“学校的油菜花开了。”
“我瞧瞧。”我趋身凑上前,她把手机伸到我下巴。
延展的画面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处各有一株树干,框出中央的焦点人物:前后两个人物,黑色羽绒服,深蓝牛仔裤,白球鞋,斜挎白布包的马尾女孩;后面那位个子娇小,白色帽T,浅色牛仔裤,手里拎着长柄雨伞,应该也是个女孩。她们在茂盛的鲜黄油菜花田梗里趑趄趔趔,又好似漫游春光,一派悠然。竹木结构的双层凉亭,我前天从图书馆二楼窗口俯瞰过。
我说:“屈老师指给我看了池塘,那个角度只看到一小块油菜花田,没想到这么一大片呀!”
应邀到四川美术学院为硕博士研究生的“艺术语言学“课程和“读写实验(第三季)—走进宋代书画世界”工作坊谈两场宋代书画文图学。第二讲主题是东亚潇湘八景诗画,听众多数有创作经验,探讨“山水”和“风景”、中西风景艺术观,特别有见解。
中间休息时间,屈波教授引我到窗前,底下两方映照天光的水塘浮现周围的树影。他说秋冬荷花枯谢了,被学校的农工清理干净,同学们跳进泥浆里徒手抓鱼,挖旁边田地的红薯,当场烤着吃!
我说两位来接机的同学让我看过那些浑身泥泞,不亦乐乎的景象照片,多么趣味盎然的校园生活!
重庆黄桷坪校区之外,新建的沙坪坝校区保留了部分原先住在这里的居民,他们维护田园,保持自然景观,成为学校的农工。“沙坪坝”,这个我几乎唯一知道的重庆地名,从小听长辈提过无数次。1997年为了抢看三峡大坝工程进行中即将没入水中的地貌和历史古迹,我在重庆登船,可惜无缘一探。
如今,就在沙坪坝的土地上,四川美术学院的校园中,依依绿柳,李花纤白,水塘之间的石桥板还寄附着青苔。淡淡三月,我想,同学们听了我的“纸上谈兵”,最好还徜徉校园,用笔墨、用镜头、用文字,留住今年的春情。
“是的。”小双介绍“读写实验”工作坊不只有学术讲座,还有临摹前人作品、个人创作、写作艺术评论和研究论文。上次(第二季)的活动结束后,举行成果展,展品包括藏书票设计,没有艺术训练根底的同学也学习木刻和印刷版画,真令我跃跃欲试!
不出校园,就有能够四季写生的素材。校外街道一路到罗中立美术馆,布满色彩缤纷的涂鸦和马赛克拼贴。校区两侧的热闹商城,也是学生分享创意的展示空间,方圆15分钟范围,浸润在浓郁的艺术气氛。不知道哪些艺术院校像这里,将“势力”扩张得如此理所当然,有美共赏。
焦兴涛教授发起的“羊磴艺术合作社”项目、王天祥教授的“行走的教育”理念,和屈波教授主编的《共在共情共生》《在地在线在场》《吾老吾幼吾生》在在显示实践“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和“中国社区美育行动计划”的意义。偏远的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羊磴镇,平凡的木工用专业匠人的手艺,打造出日常生活中的审美自觉。翻阅那些“乐在其中”的文字纪录和图像,我深深感受“无目的”的简单纯粹。
可能,我们太被求取成功的路径规范了,驯化成由外界的标准肯定自我的生存状态。
学校种油菜,是为了欣赏花?还是榨菜油?
可能,没有为了什么。
就是淡淡的三月天,一如过往。
油菜开花。我适巧路过。
2025年3月2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善若水“专栏
辯正不實之說。北宋沒有官話,有通語,接近河南洛陽,開封話
《集韻》不是口語語音書籍,是為寫作詩賦而編
我在某频道下留言指出錯誤被刪帖
爲了追求正確的知識,在此説明
“召唤苏东坡!”书法家吴耀基先生抬高双手,仰首呼喊。
我一边微笑着,一边翻看眼前一叠叠的书法作品。
流畅的草书腾跃在泛黄的竹宣纸,每一张约莫A4大小,有王勃《滕王阁序》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有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都是优雅丽致的经典佳句。
我选了“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出自王安石的《泊船瓜洲》。喜爱书法家纵横飘逸的笔势,“江”字左边的水部和“工”字距离舒展,“工”字和“南”字相近,仿佛江面开阔,岸边小舟横斜。
突然想到:有没有写苏东坡的作品呢?
书法家说:“有啊!只是这里几百张,不知道在那里?”
嗯嗯,如大海捞针,我怎好请求书法家一一翻找?
他看出我的心思,举手召唤苏东坡。
我说:“有的人有吸引出苏东坡的体质…”
然后,奇迹似的,我抽出了那张《蝶恋花.春景》: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显灵了!”
我们相顾大笑。
是的,“玄学”与否我不敢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我追寻探索苏东坡人生之路,踏上他曾经的足迹,抚触他的手泽印记,点滴积累完成《陪你去看苏东坡》,不可思议的种种经验,让我只能承认,也许世界上真的有“天选之人”。
2020年4月,《陪你去看苏东坡》台北版问世,新冠疫情全球爆发,我困守岛国新加坡,看编辑发给我的“捷报”:再版、三版、四版…,既要躲避传染,又要抢订购印刷厂纸张…。
陈文茜女士的慧眼青睐,推动读者们一窥这位花了30年岁月,只为天涯海角亲身感受苏东坡笔下的山河风景,在历史的现场凭吊千秋沧桑—我的苏东坡深情。于是,《陪你去看苏东坡》跃上畅销书排行榜冠军!记者访问我:“怎样学习苏东坡面对疫情?”我顿时哑然,谁能料到这本书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中和读者见面?为了解答记者的询问,我在新加坡政府实施阻断措施期间,闭门77天,完成《倍万自爱:学着苏东坡爱自己,享受快意人生》,和《陪你去看苏东坡》连续荣获《联合早报》年度十大好书。
台北版的《陪你去看苏东坡》因疫情之祸得福,北京版则波折连连,也是疫情影响,人事异动、编辑疾病缠身、印刷厂停工…我几乎准备和出版社解约。未知的明天会不会来?昨天的苏东坡宛若标本。
而绝处逢生的力量,还是来自苏东坡,以及许许多多的读者们。线上为纪念苏东坡生日的“夀苏会”连年举行。接踵而来的演讲邀约使我沉着反思阅读苏东坡的意义。未曾参拜河南郏县苏东坡兄弟目的遗憾终于在2024年5月弥补。所谓的“知识博主”直接拿我的书中内容当成自己的见解输出;我纠正信口开河的“想当然尔”,和对苏东坡的恶俗“趣味”及抹黑,却被博主删帖。我陆陆续续又写了十多篇文章,不只是一往情深,是责无旁贷。
于我,文章未必能高及“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至少,是心灵的滋润、是存在价值的肯定。无需解释为什么我可以透明般走过那位警卫面前,迳直到雪浪石。在被作品收藏地吉林拒绝之后,竟然能到上海观览《洞庭春色.中山松醪赋》。率意推开徐州快哉亭危楼的大门,连守门人也惊讶。我知道,此生被赋予的功课,天涯海角,因缘际会,东坡伴我行。
2025年3月15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善若水”专栏
岳飞的孙子岳珂写了一部史料随笔集《桯史》,《桯史》记载了这个故事:北宋哲宗元祐年间某天,黄庭坚拿出李公麟画的《贤己图》和其他官员一起观赏。图中画的是六七个人正围着一个盆子掷骰子,盆中五颗骰子已经停下,只剩一颗还在旋转。一个人趴在盆边大声喊叫,围观的人都紧张得变了脸色站起来。人物的细腻表情和生动姿态,被刻画得极其精妙,众人看了纷纷赞叹,觉得这画技高超绝伦。
这时苏东坡从外面走进来,斜眼看了看画,说:“李公麟是天下名士,怎么反而模仿福建人说话呢?”大家都觉得奇怪,追问原因。苏东坡解释道:“天下各地口音说‘六’字都是闭口音,只有福建人发音是张口的。现在盆里还剩一颗骰子没停,照理应该喊‘六’,但画里这人喊叫时张着嘴—这不是福建口音吗?”李公麟听说后,也笑着服气了。
以前我读到这个故事,觉得这应该是编的吧?苏东坡怎么懂福建话呢?他虽然一生宦游,多次遭贬谪,待过河南、河北、浙江、湖北、广东、海南,但是没到福建呀。难道是他同榜好友,后来的政敌,福建浦城人章惇教他的?
苏东坡说话的语音是怎样的?和现在的四川话一样吗?我一直很好奇,他走南闯北,怎么跟各地的人沟通?他和山西人司马光、江西人王安石讲什么话?
近日友人转发一段视频给我,主讲人谈的正是我的疑惑。此前我已经看过这视频,觉得推理有问题,既然友人希望求证,我便请教语言学学者,自己也做了一些研究,厘清误解。
主讲人说:“苏东坡走遍大宋天下,说的不是京城里老百姓的话,什么开封话,河南话,也不是他老家的眉山话,而是全天下读书人通用的一种很特别的话。”他拿《集韵》举例,说书里标的音“就是当时读书人的口语。”
其实,《集韵》并不是为了统一口语而编辑,更不能代表宋代的日常语音。《集韵》是宋仁宗景祐四年(1039)由丁度等人奉命编写的官方韵书,全书共十卷,按照汉字字音分206韵编排,号称共收53525字,包括大量罕见的异体字、古体字、方言字,比清代的《康熙字典》还多上万字。《集韵》以当时的雅言音韵体系为基础,是一种书面化的音韵标准,主要在规范诗赋押韵,在科举考试和经典诵读时使用。也就是说,《集韵》标的是读书音,和口语或有出入,用《集韵》标的音可以适度“还原”北宋的韵文作品。现今一些方言,比如闽南语、潮州话、吴语还有汉字“文读音”和“白读音”的区别,《集韵》里的就是“文读音”。
到了元代周德清编《中原音韵》,才算是标注了当时的口语。《中原音韵》首次用北方语音系统地整理汉字音韵,制定元曲的押韵规则,用于戏曲创作和演出,对于明清官话体系颇有影响。
宋代还没有所谓全国一致的官话,所以陕西人寇准和苏州人丁谓才会讨论天下哪里的语音最标准。寇准认为:“西洛(洛阳)地处天下中心,语音最为正统。”丁谓反驳道:“不对,各地都有方言,唯有读书人通过读书学到的语言才是正音。” 寇准采取地域决定论;丁谓则主张语言习得,他们交谈的是语音接近开封和洛阳话的通语。
苏东坡当然也必须懂得通语,他可能对方言也感兴趣,《满庭芳》词其中有“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说他在黄州度过元丰三年和六年两个有闰月的年份,家里的小辈都会说当地方言了。
他认为:“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熔化耳。”在《发广州》诗中有“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苏东坡自己注解道:“浙人谓饮酒为软饱,俗谓睡为黑甜。”两度在杭州任官,前后共五年,多多少少会一些方言,发挥在创作中,真不枉西湖的水光潋滟啊。
2025年3月1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善若水”专栏